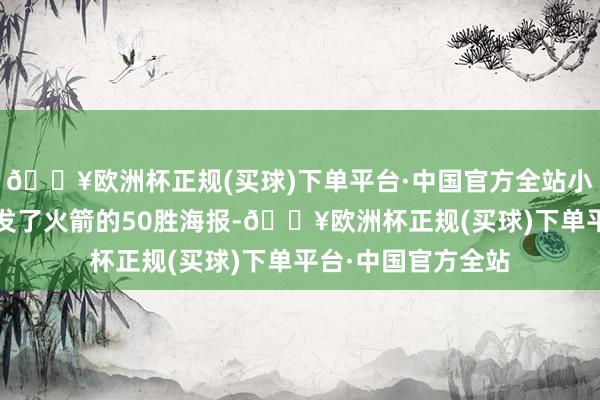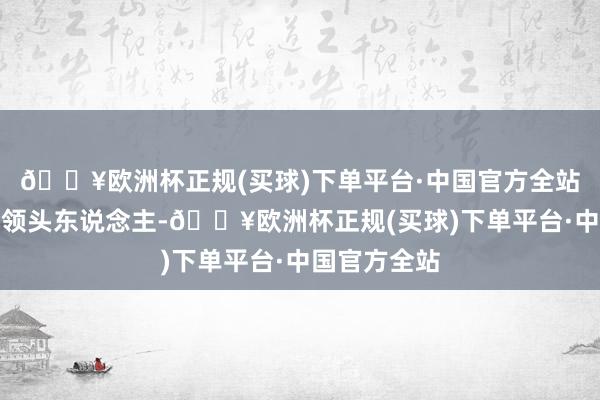刘龙:王船山《大学》证明中的“诚正相因”论探析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想主义学院讲师
选录:通过分裂“先后” 与“先後” ,王船山解构了《大学》 首章中“先后” 可能蕴含的期间接踵性维度,这为其“ 诚正相因” 论的阐明提供了逻辑前提。“ 真心当以所正之心诚之” 与“ 正心必真心” 组成船山“ 诚正相因” 论的两条主要原则。在船山的“诚正相因”论中,船山不仅反对朱子以为真心与正心两时代存在主辅关系的不雅点,还对朱子正心时代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批判。在船山看来,正心所正之心乃是仁义之心,而非知觉之心,船山的“ 诚正相因” 论体现 了对朱子学的反想和修正。
要害词:王船山;朱子;诚正相因;真心;正心
《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文件,在宋代之前,并莫得受到单独的爱好。北宋之后,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东说念主运行崇敬《大学》,《大学》的地位得以跃升。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从《礼记》中考究抽出,与《论语》《孟子》《中和》组成“四书”系统,由此《大学》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升迁,成为后世理学家所尊奉的经典之一。[1]代序3-4朱子之后的历代理学家们,对《大学》的证明可谓车载斗量。王船山对《大学》也十分爱好,他在《读四书大全说》《四书笺解》《四书训义》以及《礼记章句》等著述中对《大学》进行了详确的证明,并由此构建起我方的《大学》证明体系。在对《大学》的证明中,船山提倡“本末相因”想想。这一想想冲突了朱子、阳明等学者《大学》证明的义理藩篱,体现出船山《大学》证明的独到性和创造性。在所论“本末相因”的诸种类型中,船山对“诚正相因”的证明最为丰富、精致、深入。“诚正相因”论联结展现了船山心性骨子论和心性时代论的特色。
舍弃现时,学界尚无平直以船山“诚正相因”论为主题的征询,但在相干的一些议题上,有着比较丰富的征询效果。这些征询效果按照所聚焦议题不同可大约分为三类:一为对于船山对《大学》“真心”“正心”证明的征询1,二为对于船山对真心与正心关系论说的征询2,三为对于船山“相因”论(想想)的征询3。这些征询效果从不同的方面触及船山“诚正相因”论的多少面向。本文以船山《大学》证明中的“诚正相因”论为考验对象,旨在通过对“诚正相因”论得以诞生的逻辑前提、“诚正相因”论的基本内容、“诚正相因”论对朱子对于《大学》真心、正心证明的月旦等论题的分析,展现船山“诚正相因”论的义理架构、合座面庞与实践祥和,并以此突显船山通过对《大学》真心、正心证明所展示出的心性之学的表面与时代特色。
一、解构“先后”的期间接踵性维度:船山“诚正相因”论诞生的逻辑前提
“格物”“致知”“真心”“正心”“修身”“都家”“治国”“平天地”出现时《大学》首章,后东说念主将之概述为《大学》之“八目”。《大学》用“欲乙,先甲”以及“甲此后乙”的句式将八目表述成一个边幅接踵、顺序井然的序列;其中处在序列中的两个相邻边幅之间存在着“先后”关系。
在汉语中,“先后”是不错默示法度上的先后,亦可默示逻辑上的先后。不管是法度上的先后,照旧逻辑上的先后,组成“先后”关系的两个边幅之间都存在着期间上的继起关系。然则如果《大学》首章中所论的“先后”是这么一种含义的话,那么在《大学》八目之中,正心与真心就不存在“相因”关系;正如下文将要揭示的,在船山的论说中,“相因”的基本意涵是处在相因关系中的两个边幅之间或者相互影响。而如果“先后”具有期间上的继起属性的话,那么组成“先后”关系的两个边幅之间则只存在一种单向度的影响,即前项能影响后项,此后项不成影响前项。因此,解构“先后”的期间继起性维度就组成船山包括“诚正相因”论在内的“本末相因”论得以诞生的逻辑前提。对于《大学》首章中的“先后(後)”,船山有谓:
《大学》“後”“后”二字异用。“後”者,且勿急而姑待异日之意:对“前”字,则“先”字作在前解,而“后”者始得之意,言物格知始得至,才结束致知之功;分歧“前”字,不以时言,则“先”字亦是从彼处下时代,为此时代地之意。况云“物格此后知至”云云,乃以效之势必者言之,非云物格而後知致有次序,不可不知所後,且勿致知,待物已格而後求致知也。本文“欲”字则已有上一截时代矣,但不得纯全,故须下一截时代以成之。[2]111
在《大学》首章中,“甲此后乙”,以及“知乙此后有甲”的“后”字均作“后”,而非“後”。[3]3-4船山以为“后”与“後”的含义是不同的。“先後”即为“前后”,在“先”者与在“後”者有一种期间上继起的关系,“甲而後乙”也便意味着甲比乙具有期间上的在先性。在船山看来,“先后”与“先後”不同,在“甲此后乙”中,甲并不具备相对于乙的期间上的在先性,“先”是“从彼处下时代,为此时代地”之意。以“格物”“致知”为例,说“格物”先而“致知”后,是说从格物处下时代,自己便不错带来对致知时代的增益,格物时代的完成为致知时代的达致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这种意思上的“先后”并非是期间上的“先后”,而毋宁是一种“缓急”[4]412意思上的“先后”。其实在船山看来,《大学》八目时代是“通梢一样时代”[2]116,是不错一时并起的;是共时的,而非历时的。
这里需要指出,船山以上所论“甲先而乙后”仅仅谈及了甲会对乙酿成影响,并莫得指摘乙对甲的影响。其实既然船山承认了乙与甲的共时性,那么从逻辑上说,乙对甲产生影响便有了可能。船山确定这种可能,在船山看来,乙与甲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此相互影响即是“相因”。船山有谓:
不知《大学》时代顺序,固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煞认此作先后,则又不得。且如身不修,固能令家不都;乃不成都其家,而过用其好恶,则亦身之不修也。况心之与意,动之与静,相为体用,而无分于主辅,故曰“动静无端”。故欲正其心者必诚其意,而心苟不正,则其害亦必达于意,而无所施其诚。[4]425
在船山看来,修身时代作念不好,会导致家不成都,而不成都家,也会导致修身时代的失败。另外,真心时代作念得不好,会导致心不成正;而正心时代有颓势,也会导致真心时代的失败。船山将修身、都家,真心、正心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称作“修真金不怕火相因”[4]427和“诚正相因”[5]1487。另外,不仅修身与都家,真心与正心存在相因关系,格物与致知之间亦存在相因关系,此即“格致相因”[4]405。这种《大学》八目中出现的多少相邻两边幅之间的相因关系,船山又称之“本末相因”[5]1481或“本末相生”[5]1468。
通过对船山“相因”想想的论说,不错看到“相因”的基本含义即是《大学》八目中的多少相邻两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之意。相互影响之是以或者发生,又是建设在对乙与甲是两种相互零丁的时代的设定之上的。于是“相因”关系的存在自己亦阐明处在相因序列中的各个时代都具备本位时代,都有专属于本时代的规模和内容,不可相互取代和包含。船山的“诚正相因”论所揭示的即是真心与正心这两项零丁时代之间所存在的相因关系。
二、船山“诚正相因”论的内涵
由于船山对“诚正相因”具体机制的论说建设在其对“心”“意”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是以最初论说船山对心、意的贯穿与证明;其次分析船山“诚正相因”论的两条主要原则,即“真心当以所正之心诚之”与“正心必要真心”;临了对船山的“诚正相因”论作念出回顾。
(一)船山论心、意
如朱子所云,在《大学》八目中,“格致诚正修”属于“明德之事”,“都治平”属于“新民之事”[3]4。明德时代所指向的是个东说念主身心的修行,除却“修身”除外的“格致诚正”四时代即指向个东说念主内心的修行。《大学》对“格致诚正”的论说展示了东说念主的明德时代其已毕措施、顺序,门径,触及东说念主的说念德雄厚或说念德情绪的元素组成、作用机制以及转动旅途。《大学》提到的最垂危的雄厚温暖即是“知”“意”“心”三者,对此三种雄厚温暖内涵和作用机制的主理,乃是贯穿《大学》明德时代的钥匙。包括朱子在内的历来的理学家对此皆有大量论说,船山亦不例外。对于《大学》中的“意”与“心”,船山有谓:“然意不尽缘心而起,则意固利己体,而以感通为因。故心自有心之用,意自挑升之体。”[4]419在船山来看,意与心的内涵不同,二者是不同的雄厚温暖,有不同的情绪发期许制。
对于心,船山以为《大学》中的心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心即是“心之全体”之心,包含了《大学》所云之知、意、心,此广义的心十分于朱子“统秉性”之“心”[2]112。而狭义的心则特指《大学》“正心”章所言的“正心”之“心”。4在船山看来,比拟朱子“心统秉性”之“心”,“正心”之“心”的含义要明确和具体得多,此心即是“志”。船山有云:“故欲知此所正之心,则孟子所谓志者近之矣。”[4]403又云:“则此心字以志言明矣。正其心,常持其志使一于善也。”[2]112在船山看来,正心即是持志。对于“志”,船山有谓:“惟夫志,则有所感而意发,其志固在,无所感而意不发,其志亦未始不在,而隐然有一欲为可为之体,于不睹不闻之中。”[4]403在船山看来,志是“欲为可为之体”,具体发扬为一种恒存于心中的向善的说念德欲求倾向或说念德定向。与无意感发的意念不同,志融入了东说念主的情绪结构之中,成为东说念主的精神骨子或者东说念主格的一部分。志是知、情、意的调解,不仅体现为对价值指标感性的慎想和抉择,还包含对价值指办法豪情招供和意志对峙。而持志,即是保持善的志向以趋于至善。
对于意,船山在《四书训义》中有谓:意之发“或触于物而动,或无所感而兴”[6]66。这里船山将“意”分为两种,“触物而动”之意是东说念主在对境感物之时,心体与外物发生感应而萌生出的指向外物并期待改变外物状态的意欲,“无感而兴”之意则无谓同当下的现实外物发生关联,东说念主心不错在不雅念寰宇中构造一种外物或者情境,并萌生出意欲而指向、作用之。东说念主们在现实生存中萌生的意念大多属于后者。对于意,船山以为其“无恒体”,即意具有偶发性,与具体的特定情境相干联。意又具有“意向性”,老是指向特定的情境。特定的情境,不管是当下的现实情境,或是东说念主主不雅拟构出来的不雅念性的情境,老是倏忽易变的;意则随境而转,境生则生,境灭则灭,变动不居。
从理学家言说心性、时代时所惯常使用的“未发—已发”而论,以上所论之恒在之心(志)属于未发层面,偶发之意则属于已发层面。在船山看来,不仅未发层面有心,已发层面亦有心。已发之心即是未发之心的发用,即是情。船山有谓:
且以本传求之,则好好色、恶铩羽者,亦心良友。意或无感而生,(如不因有色现前而想色等。)心则未有所感而不现。(如存怜悯之心,无童子入井事则不现等。)好色铩羽之不妥前,东说念主则无所好而无所恶。(虽休想色,终不作好。)意则起念于此,而取境于彼。心则固有焉而不待起,受境而非取境。今此恶铩羽、好好色者,未始起念以求好之恶之,而亦不往取焉,特境至斯受,因以如其好恶之素。且好则固好,恶则固恶,虽境有远离,因伏不发,而其体自恒,是其属心而不钟情明矣。[4]417
心(志)有恒体,其存继续于未发已发。未发之时,心(志)仅仅一种潜存的说念德定向或者说念德欲求倾向;当心体对境感物之时,心(志)才感发出情;由此心(志)亦由隐变显,情即是心(志)在感物之时的清楚。比如“好恶”乃是东说念主心固有的说念德机能,是东说念主之“夙愿”[4]420场合,然则只消好色、铩羽现于东说念主前时,东说念主心才智被激励出好恶之情。从心、意各自的情绪运行机制来说,意与情皆处于已发层面,皆为对情境的感受,况且均体现了对情境的意向性,然则二者仍有区别。船山说情“受境而非取境”,是说东说念主之豪情只可手脚一种受制于特定情境条件的尽头情绪事件得以呈现,是随附于感应当下的特定情境的,体现了对情境的接管性和反应性。而与情不同,意乃是“起念于此,而取境于彼”的,即前文所提到的,意不错主动构造情境,并指向它。可见意具有投射性和决断性。
(二)真心当以所正之心诚之
船山有谓:“必欲正其心者,乃能于意求诚。”[4]403只消心志先正,真心的时代才有条件得以完成。船山云“意根心即是诚”[4]415,真心的主体,就是所正之心(志),真心乃是用心所秉之纯善无恶之志去诚之。船山又谓:
要此真心之功,则是将所知之理,遇着意发时撞将去,教他吃个满怀;及将吾固正之心,吃紧通透到吾所将应底事物上,得当穿彻,教吾意便从者上头发将出来,似竹笋般永远是这个则样。如斯扑满条达,一直诚将去,更不教他中间招致自欺,便谓之勿自欺也。[4]413
在船山看来,真心之功,一是将所知之理,介意念发动时撞去;二是将固正之心渗入、慎重5到意念之中。盖所知之理,即是东说念主致知所得之善恶之理;固正之心,即是东说念主所持之纯善无恶之志。知、志共同加持、作用于意,即是真心。又由于东说念主的纯善无恶之志自己即是东说念主将所知之仁义之理,经过持续不停的招供、内化、千里淀进东说念主的情绪结构和东说念主格结构之中,成为稳重的情绪定势的收尾;只消融入志向之中的知才不仅或者审查、判断意念之善恶,而且还能真实去影响、范导意念行动的运作,能去“撞”意。故以知真心自己便组成了以心(志)真心时代的一个内在要道,即以知真心自身也依然被包含在了以心(志)真心的时代之中。6这么知、志夹持的真心时代,最终照旧要落实到以心(志)真心,即“充此心之善,以慎重乎所动之意”上来。
以心(志)真心,也就是建设心对意的主管。意萌生之后,会资格一个发育、成长的经由,就像竹笋破土而出之后,缓慢长高一样。介意念持存、发育的每一时刻,都要用心志去控驭之。船山有谓:
但当未挑升时,其改日之善几恶几,不可预为拟制,而务于沉静修养,不可急迫迫地逼教好意出来。过甚意已发而可知之后,不可强为补饰,以涉于庸东说念主之掩著。故待己所及知,抑仅己所独知之时而加之慎。实则以诚慎重乎意,彻表彻里,彻始彻终,强固珍藏,非但于独知而防之也。[4]413
在船山看来,“意不尽缘心而起”,意有一套零丁于心志运作除外的发动机制,其萌生并非不错十足或者被心志所影响或决定。当意念未发时,东说念主对于将发之意的善恶,其实并不成有所想到或干与。此时心志唯务保持一种说念德知觉上的明朗状态,而不可急迫地试图失误出意来。而当意念萌生,参加东说念主的雄厚限制而被心志觉知之后,心志应当迅即控驭意念,尤其不成直快念而转,而迁就、装束意念。若心志对意志的控驭有涓滴缓和,那么坏心很快便会奔流决荡,如脱缰野马,决堤之河,冲破雄厚限制而发用为现实的恶行。故真心须是心志介意运作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即“彻表彻里,彻始彻终”都能主管意,不给意脱力心志适度之涓滴的契机。心志对意的控驭,最初体现为其对意的知觉、审查,并进而判断意的善恶属性。随后,如果心志认定此意为恶,那么心志便与此意交战,拿起主管,顽抗住意对心志的牵引和迷惑,摒除、阻拦此意念的发作,“急止其妄兴之念”[6]67。由于意是无恒体而随境而转,倏忽即逝的;衰退了心志的补助,并受到了心志的阻拦,不“根心”之意便莫得能源将自身进一步已毕为行动而归于消融。如果此意为善,那么心志便迅即招供、补助此意,此意取得心志的滋补与补助,成为“根心”之意。此时意取得由心志所提供的已毕自身的能源和能量,最终不错冲出不雅念限制的规模,而发用为说念德行动。
(三)正心必要真心
对于《大学》所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船山解释:“乃心,素定者也,而心与物感之始,念忽以兴,则意是也。静而不失其正,动而或生其妄,则妄之已成,而心亦随之以邪矣。”[6]48在船山看来,当东说念主未对境感物之时,即使此时心志地说念,然则在感发外物之后,感物而生之妄念有可能牵引心志,使其偏离地说念。船山又谓:
乃忽发一意焉,或触于物而动,或无所感而兴。其念善也而为之也难,其念不善也而为之也利,于是此一意者,任其择于难易锐利之间,而为善不力,为不善遂决。则将前此所知之理,素所欲正之心,欺而夺之使不得行,而远于善就于不善,是自欺其心知也。故诚其意者,使意皆出于不妄,而心为实心,知为实知,意亦为丰足之意,此后为善去恶之几决矣。[6]66
《大学》“真心”章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船山将“自欺”之“欺”解释为“凌压”[2]117。意念萌生之后,如果听任其自作东张的话,它一定会受到气禀和物欲的傍边,信赖功利原则而非说念义原则以违害就利,遂导致“为善不力,为不善遂决”。意的功利趋向会冲击、凌压志和知所蕴含的善的说念德趋向,使欢悦所蕴含的为善之志向,知所蕴含的仁义之理都不成发用出来。在志、知被意所凌压的情况下,意成了东说念主身心之主,东说念主之行动亦被功利原则所主导,而说念义原则就无法伸张。对于“意欺知”来说,东说念主介意发之时,固然清醒意念之善恶,然则由于意对知的凌压,虽知念为善而不成行之,虽知念为恶而不成遏其不行,遂出现意志胆小的情景。对于“意欺心”来说,东说念主心虽素有为善之志向,然则其被意所阻隔、凌压而不成实践,则志遂为挂空。不惟如斯,纯善之志向退隐之后,由于意的僭越,坏心则不错冒充为志,而使心志入于邪,此即船山所谓“妄之已成,而心亦随之以邪矣”[6]48。可见,意若不诚,则心不可正,故正心必要真心。
(四)船山“诚正相因”论回顾
通过以上论说,咱们不错大约主理船山“诚正相因”论的表面结构和主要内容。在船山看来,固然正心与真心两时代间有真切的关联,然则他们终归是两个零丁的时代,各有其专属的本位时代。对于真心与正心的相因,船山有谓:“则以心之与意,相互为因,相互为用,相互为功,相互为效,可云由诚而正而修,不可云自意而心而身也。心之为功过于身者,必以意为之传送。”[4]426这里船山指出了真心与正心的相因关系,即是相互为用,相互为功,相互为效的关系。盖正心时代中包含了真心时代,此正心用真心,真心时代调用了所正之心,此真心用正心;此为相互为用。心正方能以诚灌意,是正心有功于真心;真心则意不骚扰心,是真心有功于正心;此为相互为功。若心能永正,则意必诚,故正心是真心之效验;若意能诚,则阐明用以真心之心乃有充沛的说念德能源,有着确切的说念德内容,即此心定为已正之心,故真心乃是正心之效验;此为相互为效。如斯真心与正心之间之相互为用,相互为功,相互为效,即是“诚正相因”的具体内涵。“诚正相因”即是真心与正心两时代存在如上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增益,相互协作,相互撑持,相互调用,相互为对方提供滋补和条件的关系。
在船山这里,当真心、正心时代一起达致而意真心正之时,心与意又组成了一种体用的关系。此时心志为体,意念为用。“心之为功过于身者,必以意为之传送”,所诚之意就成了所正之志由情绪状态外化为实践状态的桥梁和资具。既然意为心、身之中介,是由心达身的桥梁,是以可说“自心而意而身”,而不可说“自意而心而身”。“必求其慊之实,而畅遂其向往之心”[6]67,说念德意欲在纯一至善的说念德意志的夹持下,取得充沛的实践动能,当一个个说念德意欲达成其指标之后,至善之说念德志向和止于至善的价值指标便越来越趋向于已毕。
三、船山对朱子《大学》“真心”“正心”章证明的月旦
船山对于四书的证明,是建设在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等四书学著述的消化、经受、月旦、改动基础之上的。具体到对《大学》“真心”“正心”的证明,他立基于“诚正相因”论的态度,既有招供朱子之处,亦有月旦朱子之处,这些月旦主要联结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船山对朱子对于《大学》诚正关系论说的月旦
前文依然指出,船山解构了《大学》八目时代中存在的“欲乙,先甲”以及“甲此后乙”的“先后”在期间上的接踵属性。在朱子对《大学》八目的证明中,他也不招供《大学》八目之间存在一种期间继起的先后关系。7通不雅其对《大学》的证明,不错说朱子大体将“先后”贯穿为一种“主辅”关系,至少在“致诚正”三项时代之中是如斯的。在朱子看来,就致知和真心两时代而言,则致知为主,真心为辅;就真心和正心两时代而言,则真心为主,正心为辅。[7]23-25对于船山来说,他的“诚正相因”论反对以主辅关系来刻画真心与正心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况心之与意,动之与静,相为体用,而无分于主辅。”[4]425在船山看来,心与意有各自零丁的运作机制,两者相因,互为体用,而无分主辅;相同手脚加诸心、意之上的正心、真心时代也不存在主辅关系。真心照实组成了正心时代的一个垂危要道,然则除开真心除外,正心自有本位时代,且正心之本位时代对于心正之已毕,其孝顺度不一定亚于真心。
另外,由于仍受制于《大学》“八目”的“先后”次序,朱子尽管承认“真心”“正心”两种时代不错同期进行,然则朱子仅仅指出了真心时代对正心时代的影响和增益,而未揭示出正心时代是否会对真心时代酿成影响。也即是说,在朱子这里,不错说正心“因”于真心,但似乎不可说真心“因”于正心,故这种“因”仅仅一种单向的“因”,而非船山“诚正相因”论中真心时代与正心时代相互间之双向互动的“因”。诚、正之间的双向相因是船山“诚正相因”论对朱子对于《大学》真心、正心证明的垂危冲突,拓荒了《大学》证明新的视域。
(二)船山对朱子《大学》正心章证明的月旦
在朱子对《大学》八目的证明之中,船山最不适意的就是朱子对“正心”的证明,并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月旦。大体说来,蕺山对朱子的月旦主要联结于两点,其一是以为朱子论心之含义太过浮浅。探员《大学章句》与《大学或问》,咱们发现,相较于对“格物”“致知”“真心”等条件的证明,朱子对“正心”的论说照实比较粗造。对于心果暴露涵义,《大学章句》莫得进行阐明,《大学或问》中也仅仅提到“东说念主之一心”“为孤苦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8]534对此,船山有云:“但云心者身之主,此是宽檐大帽语,直当不曾说。”[2]112在船山看来,朱子在《大学章句》与《大学或问》中对正心之“心”的解释太无极,心之含义令东说念主难以捉摸。
船山对朱子《大学》正心章证明的另一个垂危月旦是他不招供朱子正心时代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措施。对于“正心”时代,朱子《大学章句》云:“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正人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 [3]8又云:“盖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是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然或但知真心,而不成密查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3]8此处朱子用“存心”来指涉正心时代。对于朱子来说,存心即是存(涵)养,故“正心”时代即是存(涵)养时代。在朱子时代体系中,存养的时代主若是未发层面的时代。朱子云:“未发时着理义不得,才知有理有义,即是已发。当此时有理义之原,未有理义条件。”[9]2045“有理义之原”是说未发之时,心中也有浑然之理。然则此理并莫得发动出来,成为不错被东说念主心之知觉所阐明、执取的对象。在未发之时,心虽是“知觉不昧”[9]2049的,然则由于理并未发动,此时知觉便无法对理进行雄厚,是以“着理义不得”。未发之时,知觉发扬为一种悬空的阐明才略,此时只消能知,而并未有所知。8存养时代之目的在于保持知觉才略的昭明不昧,以便当东说念主对境感物之时,义剪发动之后,心体或者迅即知觉、执持、把定、哄骗之,而发用为说念德行动。未发之时存养时代的目的是为已发之后的省检或穷理时代提供知觉状态上的准备9,比方猫之未遇鼠,频繁警悟,以备遇鼠之后能立即捉捕之。总之,朱子的存养(正心)时代所存养的仅仅东说念主心的知觉义理的才略,而非义理自己。
对照前文对船山正心想想的论说,咱们不难发现,船山对正心时代的贯穿与朱子很不一样。前文依然指出,船山是以志来解心,以持志来解正心的时代。在船山看来,正心即是将致知时代所得之仁义之理不停慎重到心中,充实心之骨子,内化、千里淀进东说念主的说念德情绪结构和东说念主格结构之中,以形成稳重说念德欲求倾向和说念德定向的经由。在船山看来,能否正心,端在仁义之理能否凝固为东说念主的温煦意志。对船山来说,正心时代所存养的即是仁义之理,这与朱子之正心时代以心的知觉才略而非仁义之理为存养对象的办法是大异其趣的。船山基于我方的态度,对朱子的正心时代进行了月旦。船山云:
盖朱子所说,乃心得正后愈加保护之功,而非欲修其身者,为吾身之言行动立主管之学。故一则曰:“圣东说念主之心莹然虚明”,一则曰:“至虚至静,鉴空衡平”,终于不正之由与得正之故,全无指证。则似朱子于此“心”字,尚未的寻落处,不如程子全无忌讳,直下“志”字之为了当。[4]424
在船山看来,正心即是持志。而被仁义之理和温煦意志所充实的志乃是东说念主的说话行动的主管,故正心即是立主管的时代。由于朱子的正心时代所修养的仅仅一种知觉仁义之理的才略,而非仁义之理自己,故船山以为,朱子之正心时代并非立主管的时代,而仅仅立主管时代的助缘。由于在船山看来,心之“得正”与“不正”的凭证在充满仁义之理的温煦意志能否自作东管,而朱子所正之心仅仅一种知觉之心,而并不触及仁义等说念德内容,是以朱子的正心论也解释不了心之“不正之由”与“得正之故”。在船山这里,心之为心的根蒂,端在其有仁义之理或者温煦意志,而非有知觉;而朱子以知觉论心,这么的心便缺失了手脚心的最中枢的本质。
另外,船山对朱子“莹(湛)然虚明”[8]534“至虚至静”“鉴空衡平”[8]534等说法比较反感。10朱子所说的“莹(湛)然虚明”“至虚至静”“鉴空衡平”乃是形容心之知觉才略的惺惺不昧,无所阻拦。在船山看来,以“莹然虚明”“至虚至静”“鉴空衡平”等言心的根蒂颓势,就在于此中并不包含天理或说念德的内容;正心的指标不是让心变得何等莹然虚明,而是要心中充实着仁义之理。船山云“正心之有实”[5]1489,所谓“实”者,即是仁义之理。对于朱子所提到的孔子和孟子的“操则存”“求舒缓”[8]535的时代,船山云:“夫操者,操其存乎东说念主者仁义之心也;求者,求夫仁东说念主心、义东说念主路也。”[4]425在船山看来,东说念主之所操、所求的也不是所谓的“莹(湛)然虚明”“鉴空衡平”之心,而是仁义之心。
结 语
船山的一系列对于《大学》的证明著述看似是为羽翼朱子《大学章句》而作,但现实上却发扬出零丁的证明作风,船山建设起零丁于朱子除外的对《大学》证明的新体系。在船山对《大学》的证明中,“诚正相因”论极富表面的创造性。船山的“诚正相因”论冲突朱子对于真心、正心证明的义理模式,拓荒出新的证明视域。同期,船山对朱子真心、正心证明的批判,也体现出其对朱子学进行反想和修正的奋勉。